2010—2011年,我曾在东京大学访学,某日去逛旧书店,当我踱到“其他文学”那一架时,书架上寥寥的几本中国当代文学日译本,让人陡生寂寥之感。
如今,从刘慈欣的《三体》在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引发的阅读狂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以相对开放的心态,寻找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口”,寻找中国与世界共有、共享和共振的部分,正是中国文学“世界性”的基础。
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接受研究近年来蔚为潮流。若将“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议题在观念上视作一个载物过桥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三种不同的实践形态:当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带着主体性自觉将思考重心置于“中国文学”一端,强调的是“输出什么”,那么“海外”就会被视作异文化语境下遥望的彼岸;当我们作为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者参与讨论时,则是以立足“桥上”的姿态讨论译介、交流、传播诸问题;而在思考中国文学之海外境遇时,我们则须立足于译入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和思想语境,去观察和思考中国文学在何种程度上“进入”了异域,是油水不融抑或水乳交融?还是落地生根、野蛮生长进而成为彼邦的文化和思想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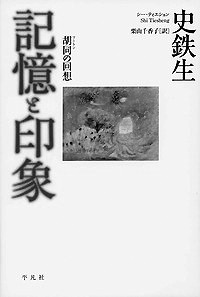
作家史铁生作品日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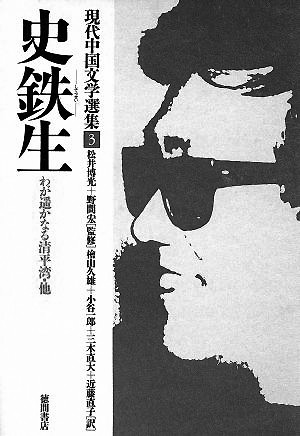
作家史铁生作品日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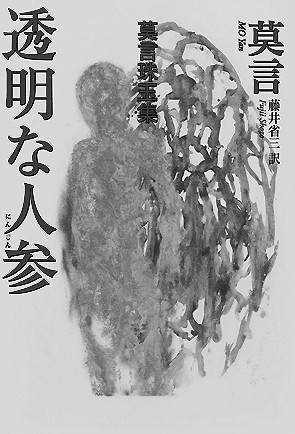
作家莫言作品日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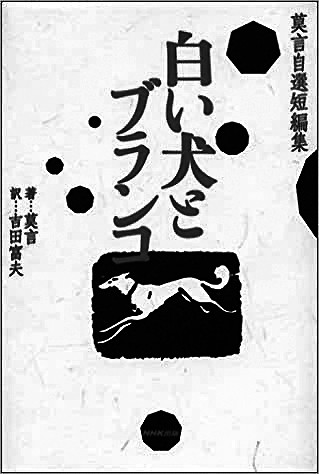
作家莫言作品日文版

学者孙歌著作日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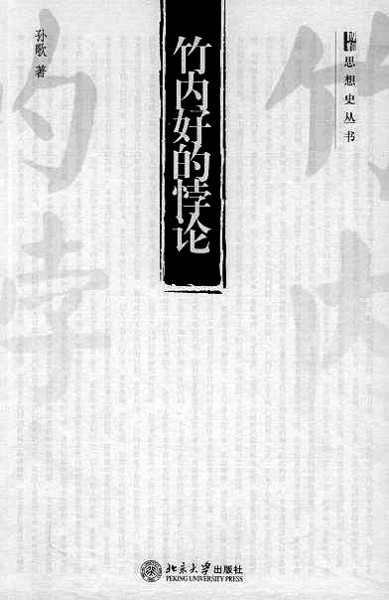
学者孙歌著作中文版
三代日本中国文学学者群像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中国文学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提供了一个理解、研究译入国文学与思想状况的异域视角,这便是外国语言文学研究者的优势所在和用武之地。
孙若圣的新著《边缘的微光:中国新时期文学在日本的译介与阐释》(复旦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微光》),就是从彼岸的视角,来观察中国新时期文学怎样被日本学者用作审视其自身的镜子。
“对古典中国的尊敬和对现实中国的轻蔑,是明治以来日本人中培植起来的一种中国观”。中国古典文学曾经是,甚至至今依然是日本人教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所谓对“现实中国的轻蔑”这一存在于近代以降日本思想史深处的基本价值取向折射到文学领域,便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轻视与漠视。
在20世纪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和接受史上,竹内好(1908—1977)是绕不过的巨大存在。他将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域外思想资源导入战后日本的思想语境中,予以重构和激活,使“中国”“中国文学”成为检视日本近代化历程及其亚洲主义观念的镜鉴,也为战后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确立了一个具有笼罩性影响的精神源头。如果说,竹内在学术与思想层面对应着一个“革命中国”,那么,如何描绘出“后竹内好(革命中国)时代”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的精神谱系,则是《微光》的题中应有之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京都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科可谓群星璀璨,会聚了竹内好、竹内实、松枝茂夫等重要学者,前后十年间他们培育了松井博光、岸阳子等一批优秀学人,而这一代开枝散叶后又在八九十年代带出了山口守、千野拓政、饭塚容等当下学界的中流砥柱,三代学者共同构成了日本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之核心力量。
《微光》在考察竹内弟子群像的同时,着力阐述了其第一个硕士生,也是始终伴其左右的衣钵传人松井博光。松井在80年代处理中国新时期文学诸课题时,确认了新时期文学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具备了世界文学的“同时代性”,同时,通过阐释中国作家的历史使命由“抵抗”向“苦斗”的转变,在“革命时代”与“后革命时代”的“同时代性”之间建立起了历史联结。
松井博光一方面援引竹内,通过强调中国文学自主产生的“同时代性”,来批判日本学界将中国当代文学比附为政治附庸的固化认识。同时,他也深知,竹内将新中国文学发展趋势描述为“后革命时代”,已经丧失了理论活力。因此,他更为强调“文革”后中国知识人的责任意识和主体性精神的复活,进而确认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同时代性”。
以健全的学术心态看待异域声音
在《微光》的第五至第九章中,我们看到的正是在国内的批评话语中已被经典化或盖棺定论的流派、作家、作品,在日本学界的另一种理解与阐释。
如在国内文坛被视为“同时代性”之代表的寻根思潮,据《微光》考证,多数日本学者都忽视或否认“寻根”的存在。井口晃就曾尖锐地指出,表面上看,中国的寻根文学确实与拉美文学一样描述着荒凉的原初世界以及对那一世界的信仰,但后者的基底中一直保持着向外部世界开放的姿态,相关作品中并不见自以为是的民族意识以及矮小的自我权威化,因此,其能够作为“世界文学”,引发广泛的共鸣。而以之为蓝本的寻根文学却止步于“返祖”,以制造荒凉与粗糙为能事,得其形而不得其神,终而沦落为无根的小把戏。而颇值得关注的是,在八九十年代,“寻根”却又被作为一种可借以接近共和国内部思想结构的隐秘路径,而被一些日本学者予以发现和阐释。
该书指出,在这一理解框架中,“寻根脱离了其在中国语境中阐释的多义性……在日本,工具性几乎是寻根的唯一属性。忽视寻根的多义性而仅仅谈论其工具性是危险的,一元化的阐释一方面轻易消解了青年作家文学创作的冲动与努力,虽然有时这种冲动缺乏节制,这种努力又过于贴近西方的各种潮流。另一方面,一元化的阐释实则大大强化了文学与时局联动的研究范式”。
必须承认,在载物过桥后,来自本土的所谓“地方性”等于“世界性”,“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乐观判断与国外学界的实际评论之间出现了奇妙的错位与乖离。观念上的正误自然是见仁见智,可是在中外学界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问题意识日渐趋同(陈平原语)的当下,我们应以学者的健全心态看待来自异域的“不同的声音”。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强调的细节——日本学者们在评论中国的寻根思潮时,甚至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亚历克斯·哈利的《根》作为参照系提示了出来。井口晃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与国内的寻根思潮进行了对比,认为中国的寻根重于术而疏于道。这一评论中的类比姿态在提示我们,桥梁的彼岸并非一个静止的异域,也并非中国文学输出的单一端口,中国也仅是日本接受他国思想文化的端口之一,在这个端口接收到的信息势必要与从其他端口接收到的信息发生交错和综合,亦须在日本文学史自有的累积和脉络中,接受包括知识阶层在内的日本民众的审视和品评。
人的文学,走向世界的“接口”
民族的并非注定是通向世界的,但世界注定要通往更广阔的天地。山口守在回忆他的中国作家朋友史铁生时说:他生活的空间如此逼仄,但其想象力却极为宏大,那是跟宇宙一样大的想象空间。在日本,史铁生是拥有最多译者和译文的中国作家。还有更多的日本学者虽未参与译介,但对其文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批评。史铁生在日本的境遇敦促我们反思“同时代性”之意义与可能。他虽然没有成为过社会瞩目的焦点,但其文学中所蕴含的深厚情感,感染了一代代的中国读者,也收获了日本学者和读者的尊重。
史铁生的作品无论抽象还是具象,不论现实抑或虚幻,其舞台都是中国这片土地。然而,他的个人叙事早已超越了现实中国社会的框架,触及人类永恒的情感、命运与困境。
山口大学史学教授池田勇太从元史学的角度对史铁生做出了解读:铁生认为如果从每个个体的“心境”出发进行探讨,那我们的生命历程绝非是可被历史书所回收之物(参见第七章),他的文学中虽不见面对现实的宏大叙事,却有对普通人的温情脉脉;虽机锋欠缺,却有傲骨存焉。从某种意义上说,史铁生乃日本学者、译者心中有关中国文学的最大公约数,恐怕亦非过言。
意味深长的是,那些带着比较意识审视中国文学的日本学者们,一旦论及史铁生,就会经常谈及自己的母亲。日本第一大报《朝日新闻》的编委白石明彦就曾说:未曾想过,在当今中国,有能写出如此蕴含着情感的散文作家,那祈祷般注视着儿子背影的母亲之眼神,令人感到心痛。母亲、母爱虽不可能成为讨论中日“同时代性”的辐辏焦点,但却是超越时代的永恒母题。
《微光》提示我们重思中国文学之“世界性”的双重指向与可能:在新的观念与技法层面,中国文学或许不得不长期扮演追赶者的角色;而在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永恒母题上,在“人”的宿命与通向未来的意义上,又可以心同此心、不落人后,史铁生、刘慈欣等在日本受到的追捧皆可作如是观。越是“人”的,也就越是“世界”的。以“人”之名,或许才能获得让“世界”倾听的语言,才能找到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接口”。
《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30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