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中总有一些用不俗的名词,“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等都是这样的词汇,每个民族的文学史中似乎都有被这样命名的时期,而此类名称所指的繁荣或珍贵又绝不仅限于文学范畴。
如今,被冠以“白银时代”之称谓的一段俄国文学和文化,又突然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和热门的出版选题,报刊上以此为题的文章不断亮相,光是以“白银时代”为题的丛书就接踵出了四套:作家出版社“白银时代丛书”六种,学林出版社“白银时代俄国文丛”五种,云南人民出版社“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七种,中国文联出版社“俄罗斯白银时代精品文库”四种,真可谓热闹非凡。这样的场面,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从阅读客体的角度看,20世纪之初的俄罗斯文化的确是五彩缤纷、硕果累累的。

《白银时代的星空》 刘文飞 著 北京出版社
“白银时代”,天才又一次成群而来
在“白银时代”,帕斯捷尔纳克所言的“天才成群地诞生”的罕见现象又一次在俄国出现。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那短短的20余年时间里,俄罗斯却向20世纪、向全世界贡献出了一大批的大师与杰作,并为诸多文化门类在20世纪的走向开了先河,如哲学中的宗教存在主义、文学理论中的形式主义、诗歌中的阿克梅主义,还有美术领域的康定斯基和音乐领域的斯特拉文斯基等等。那的确是一座文化的富矿。可以说,在当今的俄国,“白银时代”也同样是一个新的阅读热点。
另一方面,从我们主观的角度来看,中国读者对俄罗斯的文学和文化一直有着一种较强的“阅读期待”,于是,我们将期待、选择的目光投向绚丽却又陌生的“白银时代”,乃是十分自然的。当然,促使我们关注“白银时代”文化的,也许还有在20世纪之末梳理20世纪文化遗产的某种潜在愿望,还有对“世纪末情结”有可能在“白银时代”文化中得到抚慰、赢得共鸣的某种希冀,还有学术圈欲描绘出一幅20世纪俄语文学完整画面的刻意努力等等。客观的、主观的原因,必然的、偶然的因素,共同制造出了当前这个“白银时代文化热”。
我国学者关于“白银时代”的讨论也很热烈,单就“白银时代”这一称谓的来历,就有诸多意见。在是否使用“白银时代”这一概念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至今仍有一些学者很反感“白银时代”的提法,认为它并不构成一个“时代”,他们很留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的概念,似乎一使用“白银时代”就是抬举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就是让它与其前辉煌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其后繁荣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平起平坐了。其实,将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者,如索科洛夫等的研究成果与当今有关“白银时代”的著作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它们在研究的范围和对象上并无太大的差异;再者,“白银时代”文化的总体倾向与其前、其后文化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不能因为其持续的时间短而忽视其独具的内涵和外延。显然,“白银时代”不构成一个时代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目前对“白银时代”这一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有两种倾向值得关注:一种倾向是将“白银时代”的内涵宽泛化,另一种倾向是将“白银时代”的性质意识形态化。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通常是指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之后和苏维埃文化之前这一时间段中的文化,它横亘在两个世纪的交接处,时间跨度为20余年。关于“白银时代”的分期,目前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它大致的起止点还是得到了比较一致的界定,即托尔斯泰之后和十月革命之前。当然,你可以说与托尔斯泰的后期创作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安德烈耶夫等人的创作就已经显现出了与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有所不同的一些特征;当然,你还可以说,十月革命并未能截然阻断“白银时代”的文化惯性。任何一个时代都与其前后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一个时期的划分因而也都是相对的。
相比较而言,“白银时代”的划分倒还有着更为牢靠的依据,因为,作为其开端的俄国象征主义诗歌运动,有着与传统俄国文学迥然不同的美学风格和艺术趣味,而注重个人价值和艺术创新的“白银时代”文化必然会在不久后迅速中止。面对这样一个相对清晰的文学史分期,我们的一些学者却仍想做某种“扩大化”的工作,试图尽量拉长、抻宽“白银时代”。有人欲加大“白银时代”的规模,认为其上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下限为斯大林时期的开始;有人则欲增加“白银时代”的内容,认为它不仅应该包括当时已近尾声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新起的无产阶级文学,而且还应该包括普列汉诺夫等的社会主义学说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学说。
此外,在低估或高估“白银时代”的人士身上都出现了一个“时代倒错”现象,即忽略了“白银时代”是出现在十月革命之前,完全依赖其与之后时代的联系或其在之后时代中的命运去看待它,这是难以对它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的。我们听到了关于“白银时代”文化为“颓废”文化的指责,我们听到了关于那一时期的作家“世界观落后”“脱离人民”的说法。事实上,纠缠在文化与专制之冲突这一点上,并将这一点视为“白银时代”文化之“重点”,是不恰当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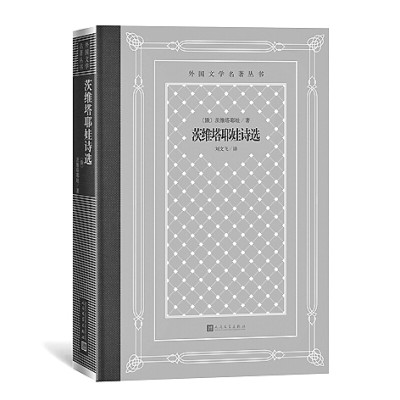

画家伊萨克·列维坦的风景画。资料图片
创造的时代与“文明的孩子”
俄国“白银时代”文化的主要意义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认为,首先,体现在那一时代的艺术家所体现出的空前的艺术创新精神。俄国宗教存在主义者在20世纪之初开始了对现代意义上的存在问题的思考,自他们开始,“生存意义”“终极关怀”等命题成了20世纪现代主义哲学的主要内容;俄国形式主义者在20世纪之初开始了对文学“内部规律”的探讨,文学研究开始了其“科学化”的历程,文本、语境、词,乃至声音和色彩,从此成了精心研究的对象;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未来主义是20世纪之初俄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三个主要潮流,它们风格不同,主张各异,但在进行以诗歌语言创新、以在诗歌中综合多门类艺术元素为主要内容的诗歌实验上,它们却表现出了共同的追求;从康定斯基起,绘画的“三要素”被否定了,原来可以用点来构成线,用点来构成面;从斯特拉文斯基起,音乐的单阶被彻底重建了,“十二音体系”极大地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如今,人们意识到,20世纪是一个文化艺术上的现代主义世纪,而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每个艺术门类的“现代化”都与20世纪之初的俄国有关,这不能不让人感叹“白银时代”俄国文化人巨大的创新精神。“白银时代”将作为一个“创造的时代”而载入人类文化的历史。
其次,在进行空前的艺术创新的同时,这一时代的人也保留了对文化传统的深厚情感,只有以俄国未来主义诗歌为代表的“左派艺术”对文化遗产持否定态度,而那一时代大多数的文化人无疑是珍重文化传统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一次在回答“什么是阿克梅主义”的问题时说:“就是对世界文化的眷念。”这个回答是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意义的。在那个时代,远至古希腊罗马的神话,近至德国的哲学、法国的象征主义理论,都为俄国的知识分子所关注,尤其是在“白银时代”俄国知识分子的身上一直有着比较充分的体现。因此,他们敢于以世界文化的捍卫者自居,他们在北疆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命运做温暖的思考。
最后,与对文化的眷念相关,“白银时代”的文化人普遍显现出了一种心灵的真诚。20世纪之初是一个动荡的时代,革命与战争此起彼伏,那也是一个混乱的时代。然而,就在那样的时空中,俄国的知识分子却体现出了布罗茨基所言的“文明的孩子”的赤子情怀。在兵荒马乱的岁月,他们居然能专注地端坐在书房里,潜心写作;在欲望膨胀、价值重估的年代,他们始终保持着对艺术价值和自身价值的坚定信念;在充满彷徨和疑虑的世纪之交,他们在匆忙而又认真地整理着过去世纪的文化遗产,并同时为新世纪文化的走向确定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许无法扭转当时的社会风气,但他们却保持了文化的繁荣和延续。他们的思索和发现也许不是纵贯世纪而皆准的真理,但他们精神劳动的成果显然没有在百年或更短的时间里“随风而去”。如今,在功利原则深深侵入文人生活时,20世纪之初俄国文化人的那种心境和信念是尤其让人感动和羡慕的。
在热烈地谈论“白银时代”文化的时候,我们也要保持一份冷静。在阅读中,往往有最新的东西就最时髦就最佳的定式选择;在研究中,填补了的空白往往更受推崇,一些研究者又总会在有意无意之间将自己喜爱、熟悉的对象“唯我独尊化”。目前,大部分研究者似都在毫不吝啬地鼓吹“白银时代”。相对而言,关于“白银时代”的冷静看法则较少。比如,与极具公民责任感和道德感的俄国文化传统相比,“白银时代”的文化显得过于关注自我和内心、过于贵族味了;再比如,在关注世界文化遗产的同时,“白银时代”文化对俄罗斯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和整理则相对较少,等等。只有在注意到并思考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才可能对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文化有一个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画家伊里亚·叶菲莫维奇·列宾的人物速写。资料图片
阅读链接
刘文飞译《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是商务印书馆“俄语诗人丛书”之一种,本书从帕斯捷尔纳克的抒情诗中选译50首最著名诗作,并以俄汉双语形式出版。
《茨维塔耶娃诗选》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网格本·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之一种,选译了茨维塔耶娃的300余首抒情诗,另收入她最著名的两首小型长诗《山之诗》和《终结之诗》,译者刘文飞在《译本序》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茨维塔耶娃这位白银时代独具特色的俄语女诗人多舛的命运和杰出的诗歌创作。
《光明日报》( 2022年03月31日 11版)